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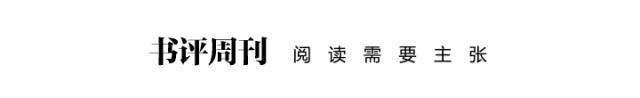
多和田叶子是日本当代著名小说家,她的名字曾经屡次在诺奖的赔率预测榜上出现。使用日语和德语写作的她拥有令人惊讶的思想视野,而她也非常擅长运用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动物的形象,将大量现代社会与现代人内心存在的问题投射出来。

多和田叶子,1960年生于东京。小说家,诗人。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系毕业。1982年起在德国生活,用日语和德语写作。1993年获芥川赏,2018年获美国国家图书奖·翻译文学奖。

撰文 | 宫子

北极熊的记忆
“异化”是我们现在经常讨论的一个词语,我们能找到大量文章论证现代社会对人的异化,工作对人的异化,历史对人类群体的异化等等,哲学家齐泽克还在之前提出了创造性工作对人的异化。哲学与社会学著作已经对这个概念有着足够深刻的论证并且时常提醒我们保持警惕,注意身边那些任何有可能将我们引入异化的事物——事实证明,它们占据绝大多数。而文学的作用永远是关注人类自身,因此小说从功能性上可以说弥补了逻辑思维所并不承担的一个空缺,那就是提醒我们:自我是如何将自我异化的。虽然我们可以说任何自我的异化都有一个根源,但在小说叙事内,自我理应是一切的源头,格奥尔格会异化成一个甲虫当然和彼时奥地利犹太人的处境有关,但在《变形记》里,格奥尔格就是在自我的哀叹声中变成了一只甲虫,甚至还有那么短暂的几秒钟为此感到舒适。日本作家多和田叶子也许是最擅长在这方面发挥想象力的作家,她在《雪的练习生》中通过三代北极熊的故事为我们展现了这一点。
《雪的练习生》
作者:(日)多和田叶子
译者:田肖霞
版本:译林出版社 2025年3月
《雪的练习生》是用北极熊的视角写成的。在文学史上,动物们已经承担过太多的文学角色,当它们这样毛茸茸地出现在小说中时,一般就等于告诉我们,这个故事要么是个童话,要么就是一种针对人的异化(《少年Pi的奇幻漂流》所引起的两种结局讨论的本质正在于此)。而多和田叶子所写的《雪的练习生》通过丰富的故事视角,让这部以动物为主人公的小说具有了去人类中心的现代叙事色彩,同时又在塑造小说的过程中令我们不断感受到人类社会的存在。
小说中最早出现的北极熊是作为外婆的“我”。外婆北极熊出生在苏联,没有什么对母亲和北极的记忆,自从她记事开始,负责看护抚养自己的就是一个叫做伊万的驯兽师。伊万不断驯化外婆北极熊,将她培养成一名苏联马戏团的演员。他所使用的办法非常老套而有效,他在北极熊的后腿绑上奇怪的东西,然后再配合鞭子让外婆北极熊学会站立,等到外婆北极熊长大一点后,再通过重复训练培养条件反射,让外婆北极熊认为四肢着地会令地板疼痛,于是努力挺起上半身,最终学会了站稳。在正式演出的时候,伊万会在舞台下方的地板点火,让地板变得滚烫,天生喜爱冰冷的北极熊无法忍受滚烫的温度而抬起前肢,同时伊万再给外婆北极熊的两个后腿穿上有隔热功能的鞋子,搭配驯兽师“站起来”的口令和响起来的交响乐,就这样完成了一场又一场马戏团演出。事后,表现好的外婆北极熊会从伊万那里获得一块方糖。再之后,外婆北极熊逐渐学会了骑三轮车等动作,而且形成了对世界的认知,“我渐渐明白了,世上有三种动作。会带来方糖的动作,会让鞭子飞过来的动作,没有鞭子飞过来也没有方糖的动作。就这样,我的头脑有了三个抽屉,外来的邮件会被分门别类地放进那三个对应的抽屉”。
一块方糖在驯化过程中所承担的角色是极重的,同时也是神奇的,因为这个世界上并不只有成功执行驯兽师口令所获得的方糖,还有自己想要获得更多方糖的欲望。后者往往是更好也更有效的驯化催动。在膝盖受伤后,外婆北极熊便无法再从事马戏表演的工作,按照惯例她即将被射杀,但所幸得到了一份管理岗位的工作,大量的会议让外婆北极熊感觉生活布满了霉斑,在她第一次推掉了会议后,担心随时会被抹杀的外婆北极熊开始尝试书写自传,将自己的生命记录下来。她本以为,这是一项重新找到自由生命的机会,但没想到结果却并非如此。她首先去找了海狗,本来她只想把简单的自传作为私密的事物分享,但海狗读了后觉得有出版机会,让外婆北极熊多写点。外婆北极熊觉得写不写、写长还是写短完全是自己的自由,海狗却从办公室抽屉里拿出了西方的巧克力,并表示继续写的话就会不断得到巧克力。在外婆北极熊不知情的情况下,海狗出版了她的自传,还取了非常浮夸的标题。外婆北极熊本来非常气愤,但无意间成为自传作家所收获的成功感成为了她人生中彻底无法摆脱的另一块巨型方糖。“我虽然对海狗生气,但成为作家的喜悦让我彻底被他的陷阱钳住脚踝,没法自由行动。海狗那一类的家伙大抵在中世纪就已经掌握完美的陷阱制作技术,他们用陷阱捕熊,给熊戴上花环,让熊在路上跳舞。民众开心地鼓掌喝彩,向他们抛出金钱”。
逐渐地,方糖开始成为一种欲望。之后,为了避免被送到西伯利亚种橘子,外婆北极熊找机会去到了当时的西德。在那里,作为奖励的方糖从巧克力升级成了北极熊最爱吃的烟熏三文鱼,西德的负责人给外婆北极熊提供三文鱼,而后要求外婆北极熊在他们的国家写抨击苏联的自传。这个桥段的故事为我们展现了另一种无法避免的异化,外婆北极熊在苏联马戏团感受到了人生的束缚,她为了证明自己不是一头只会表演的北极熊而开始写自传,证明自己人生的存在。但是在当时的西方国家,她追逐自由的举动却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种异化。在西方世界眼中,她写的东西到底是不是真正的自由,甚至她写的东西是真是假都无所谓,外婆北极熊不可避免地被塑造成异乡人的身份,西德负责人们想要的只是一本能够抨击苏联政府的自传。西德政府的人甚至精心维护着外婆北极熊那个“苏联流亡者”的身份,当外婆北极熊想要学习德语时,他们并没有兴趣,他们更希望外婆北极熊坚持用俄语写作,成为一个完美的流亡作家。西德的记者希望采访外婆北极熊,聊苏联的人权问题,但外婆北极熊表示自己从来没思考过“人权”问题,因为她不过是一头北极熊,是一只动物。多和田叶子再次在小说中利用了北极熊的动物形象,将异化的人和流亡主题串联在一起。在北极熊的眼里,人权只是属于人类的,而从未听说过自然万物拥有什么权利,这个动物形象将流亡、冷战对立、意识形态等政治问题收拢到关于生命本身的思考中。在关于什么是真正的自由这一点上,外婆北极熊曾经浏览过世界各国招待“流亡者”的条件,他们都承诺会提供温暖的住所——然而,外婆北极熊对此感到恐惧,作为一头北极熊,她最想要的是一片冰雪世界。这是她真正想回归的自由,但是,不会有任何地方对此给予承诺,毕竟在人类的意识形态中,辛苦建构的自由世界怎么可能是冰冷的呢?
无法复原的异化
外婆北极熊之后则是女儿托斯卡的故事。在托斯卡的故事中出现了一个名叫厄休拉的女人,与外婆的遭遇不同,托斯卡遇到了也许是唯一能够真正理解北极熊的人类。然而,作为小说里的一头北极熊,她象征着异化过程的不可逆,尤其是在他人的目光中,一旦被视为异类,那么几乎没有被正视的可能。小说中的北极熊作为一个动物形象出现,可以说从登场的那一刻开始就决定了北极熊人生的悲剧性。
如果说外婆的故事主题是流亡与虚伪的自由,那么托斯卡的故事则反映着情感的隔阂与人类社会对个体权利的漠视。托斯卡生活在东德的马戏团,与母亲相比,托斯卡的境遇要稍微好一点,因为人们开始从某种程度上重视明星动物了——但目的也很明确,就是为了让他们做出精彩的表演。第二章讲述了大量厄休拉的故事,多和田叶子在小说中对此给出了解释,那就是当厄休拉决定要为北极熊托斯卡写一本传记的时候,却发现写的大多是自己的故事,而托斯卡则表示无所谓,因为只有当厄休拉能够写好自己故事的时候,才会有空间来写自己的故事。因为托斯卡明白,自己的生命只有厄休拉的情感能够理解。在这个故事里,厄休拉似乎拥有一个不同常人的超能力,那就是她能够敏锐地洞察到动物的情绪。她的丈夫是一个驯兽师,曾经训练过狮子和棕熊,但是有一天她比丈夫先发现棕熊的情绪不对劲——那头棕熊仿佛意识到日夜相伴的驯兽师其实对自己并没有真实的感情,于是棕熊开始出现危险行为。厄休拉虽然也从事训练动物的工作,但她非常在意和动物之间的心意相通,她认为驯兽师具有力量的并不是挥舞的鞭子,而是与动物之间的情感。
已经有大量文学作品或者正面或者侧面地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对于异化形成的群体矛盾最好的解决办法便是向其中注入真实的情感。假若有人愿意拥抱卡夫卡的那只甲虫,格奥尔格也不至于在饥饿中死去。然而这也恰好是文学被诟病为软弱的地方——它一直如此期许,却从未实现。对人类来说,从情感上尝试理解对方似乎是比任何伟大发明都更加困难的事情。在小说的这个章节中,出现了一群来自西德的白熊,他们来到马戏团后组建了一个劳工工会,要求马戏团改善自己的工作条件,其中包括提供带冷水的浴室等等。马戏团的负责人完全无法理解白熊的这些要求,最终有一个人想出了办法,他通过钻漏洞的方式加入了白熊们的劳工工会,然后用股份制和分红等方式引诱白熊,最后以白熊们不再属于劳工而属于资本方的理由让白熊们的要求彻底瓦解。在这样的环境中,托斯卡自然不会拥有太多被理解的空间,马戏团的人们甚至想着要让她表演写字,表演更加具有难度的节目,人们认为她有这方面的天赋——因为她的母亲是一头著名的马戏团北极熊,而“表演是会遗传的”。异化与驯化的差异正在于此,驯化更多在群体的层面体现且具有生命的延续性,小说中对此的论证则是历史上第一个人学会了走路后,后代们也紧跟着学会了走路。具有马戏团世家背景的托斯卡正是走入了这样一个无法摆脱的命运。
在小说的最后,厄休拉和托斯卡决定来一场未经报备的、惊世骇俗的表演。她们在马戏表演的最后一幕登场,然后在全世界的镜头前来了一场接吻。这个吻意味着厄休拉以人类身份对托斯卡这头北极熊所发出的共鸣。但在世界镜头的传播中,共鸣被消解了,人们更多讨论这个吻的共鸣所带来的传染病等问题。也许一两个生命之间的共鸣是可行的,但群体之间的共鸣却如此艰难,另外人类社会还发明了一种更加邪恶的存在,那就是控制这种共鸣。也许是为了避免后代在这种继承驯化的命运中循环,在生下后代之后,托斯卡拒绝了哺育的义务。
图/IC photo
克努特的悲剧
如果我们对2000年末的新闻还有印象的话,一定会记得当时的新闻经常播出一个德国的明星动物——一头叫做克努特的小北极熊。《雪的练习生》的故事正是以这个现实案例作为范本而完成的。现实中克努特的确有一个叫做托斯卡的父亲(背景也是出生于苏联、来自东德的马戏团),而且那头叫做托斯卡的北极熊现实里也拒绝了养育后代的义务。于是,小北极熊克努特只能被德国柏林动物园人工饲养。
在当时,小克努特凭借着新闻镜头里呈现的可爱形象,成功在2000年代引起了世界范围对于温室效应的关注。它成为了北极熊这个群体的形象大使。与外婆和母亲的命运不同,生活在现代社会的小克努特不用再担任马戏团演员,动物园内有专业人士精心照顾它,然而,他们同样对小克努特抱着功利性的期待,那就是希望它能以可爱的姿态唤起人们对环保问题的关注。
小北极熊克努特。
《雪的练习生》中所讲述的克努特的故事正是对这一问题的描述。这头拥有世界上最高知名度的北极熊是人类的宠儿,但是,克努特遇到的问题是它的外婆和母亲都未曾遇到的,那就是克努特已经彻底被“偶像化”了。在媒体传播的过程中,克努特不再是一头真正的北极熊,而是成为了一个名叫克努特的可爱北极熊形象,似乎唯有可爱的小北极熊这种形象才能够唤起人类对北极生态问题的关注。克努特的饲养员马蒂亚斯也知道这一点,虽然他自己并非特别情愿,但还是尝试将克努特往可爱的印象上进行引导。小说中他尝试带着克努特练习玩皮球,但克努特其实更喜欢玩摔跤,“我不喜欢任何一只球,譬如那只写有‘全球化、革新、沟通’的黄球,散发着一股不可信的橡胶味,我连碰都不想碰。但据说那只球是某位大人物赠送的,一旦我不理会那只球,马蒂亚斯就明显开始焦虑’”。
现代社会的偶像化或许也是异化的一种表现,只是人们看待偶像化个体时的态度会更具热情一些——但也仅限于当下——偶像化的问题在于人们无法接受这个形象的变化,偶像化的个体并不被当作生命体看待,而被视为一种奇特的永恒物。如果说人类尚且能够依靠理智与行为来控制这一点,让自己固定在偶像化的琥珀中的话,那么作为动物的北极熊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于是在《雪的练习生》中我们可以读到,当小克努特的年龄逐渐长大,在一次与饲养员的嬉闹中无意抓伤了人类时,人们立刻意识到这头小北极熊已经不再可爱,它具有野性,它存在危险这些之前不曾思考过的问题。抓破了偶像化身份的克努特立刻被用另一种方式观察对待。人类开始对它具有敌意,而当克努特感觉自己实在过于疲惫,不愿意继续在动物园里表演下去的时候,人们也就不再把它当作明星克努特对待。此时,只有参观动物园的小孩子能感受到这头北极熊的难过,而大人们则残酷地表示,“你看它的利爪,听说它弄伤了饲养员”,“它已经不可爱了”。
而在现实中,小克努特于2011年3月9日猝死——就在多和田叶子这本小说出版的两年之后。直接死因为溺水,一种对北极熊来说难以理解的死因。根本原因在于克努特患有严重的抗NMDA受体脑炎,这种疾病会产生严重的精神问题。
在那个可爱的小克努特狂热席卷全球的年代,我们可以说多和田叶子是罕有的、知道小北极熊并不快乐的人。而她只是通过文学幻想的情感共鸣捕捉到了这一点。
有时我们必须得承认,人类的情感有很多时候要比人类自诩独有的理智更加冷静。理智经常为我们构建出一套疯狂的行为体系。在《雪的练习生》中小克努特的章节里,多和田叶子写了一件当时真实发生的事情,那就是以德国动物权利活动家弗兰克·阿尔布雷希特为代表的一小批人曾经提出建议,柏林动物园应该给小克努特实施安乐死。一个动物权利活动家居然会要求动物园处死一个动物,这听起来非常难以理解,而他们的逻辑是,人工饲养的动物已经失去了动物的天性,这是对自然的一种损害,所以应该杜绝这种行为,对人工饲养的动物实施安乐死。这是小克努特无论如何都无法理解的人类行为,它永远无法理解在人类社会中、逻辑可以成为任何社会与政治行为的辩护律师,它只想沉浸在自己最喜欢的冬天里,看着雪花一片又一片落下来,但很可惜,多和田叶子所书写的结局,并不属于这个已经被偶像化的北极熊。
如果没有人类存在的世界
人类社会所构建的荒诞与异化在多和田叶子的多部小说中都有所呈现。在2018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小说《献灯使》中,多和田叶子就在几个故事里描绘了末日社会的景象。《献灯使》的故事都具有着明显的多和田叶子风格,对人类社会的悲观,从末日视角审视的人性,以及从词语本身引发的思考,多和田叶子的小说似乎唯一的缺陷在于她并不是特别擅长为想象力铺张的小说结尾,总是将小说的结局散向天空。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末日故事也很难有真正的结尾。
《献灯使》
作者:(日)多和田叶子译
者:蕾克
版本:野spring|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5年1月
在《献灯使》这个小说集中,多和田叶子描写了世界的倒退,当然作为日本作家,她重点描写的必然还是日本社会的倒退,其中包括在福岛核电站泄漏后,人们的恐慌和核辐射造成的危害。小说中的日本政府在核泄漏后彻底崩溃,网络通讯陷入瘫痪,同时多和田叶子还描绘了另一种意义的死亡,在小说中,老人们因为遭遇核辐射而获得了“永生”,辐射导致的变异让他们永远都无法自然死亡,从而变成了被诅咒的人,他们照顾自己一代代的子孙并目睹他们衰老离世,而自己却只能永远停留在这个世界上。这种核辐射导致的“永生”反而在小说中成为了极具冲击力的创伤形象,也让小说得以从日常生活着手描绘出末日后的社会变异景象。在同名短篇《献灯使》中,日本社会进入到了一种诡异的状态,一方面体现在多和田叶子对词语的捕捉,这是现代社会的特点之一——词语的寿命比以往更短,大量词语由于对应时代的逝去而不再被人们使用,例如小说中“慢跑”这个词已经作为外来语在日语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私奔”,但同时由于时代的变化,“私奔”一词又不再和恋爱产生任何联系。但另一方面,末日之后的日本所呈现的又是原始化的景象,也许是对工业产生的恐惧和后遗症,小说中的日本人因为担心数据泄露而不再使用电子软件,反而使用手写的方式来进行记录,这样既不会泄密,又不会发生所有数据在瞬间被篡改抹除的危险。末日后的日本也与世界发生了割裂,国内重新实行了闭关锁国的政策,人们完全无法了解日本之外发生的事情。小说“献灯使”的得名也来自于此,“献灯使”一词在日语中和“遣唐使”的发音相同,小说中也出现了一个秘密组织,他们偷偷将孩子们作为“遣唐使”送出日本,希望他们能够看到世界应有的模样,从而为改变日本的异化社会保留希望。
在另一个故事《动物的巴别塔》中,人类社会则彻底消失,动物们开始聚集在一起讨论人类曾经带来的压迫和没有人类的新世界规划。但是动物们在准备建立新世界的时候却发现自己正在陷入人类过去的社会建构模式,最后,动物们集体讨论人类灭亡的原因。按照多和田叶子的设想,这出戏剧在结尾时会播放提前制作的随机采访视频,让音量越来越大最后形成一片雨声,来让观众反思人类社会灭亡的原因。同时,还会有大量的字典从天而降,让观众们从舞台上带走。字典也是多和田叶子文学思考的一个重要方式,在她的小说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如何在词语的分裂中产生对现实状况的迥异认知。
可以说,多和田叶子的大部分小说所构建的氛围都是非常诡异的,她的小说风格具有浓重的空想色彩,却又不像村上春树那样徘徊于两种哲学对立的边界。她所描写的末日世界和异化的人类社会触及了大量现实问题,但是我们似乎完全无法从中找到症结,因为它就好像是我们此时此刻正在经历的世界现实一样,如果说世界是令人困惑、让人无法拥有清醒认知的话,那么小说产生相应的困惑氛围也就不足为奇。同时多和田叶子也让我们看到了清醒的逻辑会如何将人类引向异化。
多和田叶子所构建的架空世界中的某些部分未必不会成为现实,就像我们总是说世界上疯癫的事情总是越来越多一样,她小说的悲剧性就像是古希腊的预言,不过,神话中每个知晓预言的人都没能摆脱预言的命运,而神话时代之后的我们在今天也许同样如此。小说只是用各种形式向我们传达着这一点,踏入人类社会的北极熊们最终没能回到北极看雪,我们也很难在现实生活中找回真正的自我,无论我们有多么愿意讨论后者这个话题,那块方糖早已经取代了我们真正赖以生存的冰山。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作者:宫子;编辑:张进;校对:薛京宁。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最近微信公众号又改版啦
大家记得将「新京报书评周刊」设置为星标
2024书评周刊合订本上市!
点击书封可即刻下单
配资靠谱证券配资门户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